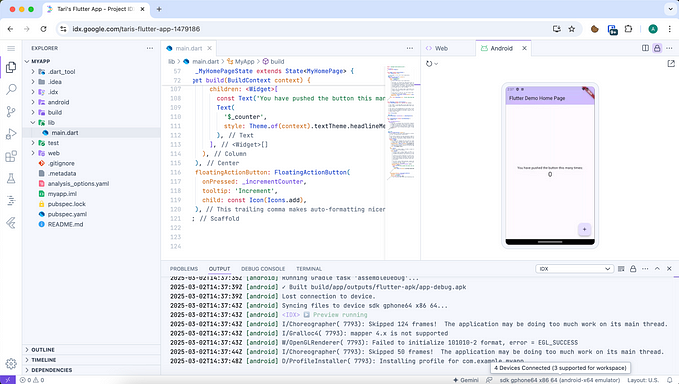廢墟攝影的案例寫作

文︱陳寬育
廢墟,無論是做為具體物質現象或是一種供凝視與思考的概念,都不是在當代才初次獲得聚焦式的極大關注;廢墟做為觀看對象,它其實有很長的歷史。尤其是,廢墟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期甚至還特地被「建構」、「創造」出來,以一種哲學性空間的狀態,成為提供「懷舊」(nostalgia)與「憂鬱」(melancholia)的哲思對象。此時,廢墟變成一種「功能」,這是某種確保當前現實的合法性,以便朝向一個更理想的未來的實踐手段。
理論家艾德瓦多.卡達瓦(Eduardo Cadava)2001年發表於October期刊,論廢墟影像的文章,展示了「廢墟的影像」與「影像做為廢墟」之差異,以及廢墟敘事的某種的不可能性。「廢墟影像見證了許多難解的關係――例如死亡與存活、失去與生命、毀壞與保存、哀悼與記憶。廢墟影像也告訴我們(如果它還能告訴我們些什麼),無論在廢墟影像中死去了什麼、失去了什麼、哀悼著什麼,即使它們仍掙扎著存活與存在,其實都是關於影像自身。這也是為什麼廢墟影像如此常訴說著死亡,其實就是影像的不可能性。它宣告廢墟影像沒有能力說故事,例如訴說廢墟本身的故事。」(註1)
因此,卡達瓦認為,各種關於廢墟的影像――無論是構成廢墟的、屬於廢墟的、從廢墟觀點出發的、試圖訴說廢墟的,所有的廢墟影像都不會只是影像自身,更是「廢墟的廢墟」(the ruin of ruin)。但是,我們如何理解廢墟攝影的影像是「廢墟的廢墟」?卡達瓦寫道:「廢墟透過影像的出現與存活,告訴我們它不再能展現任何東西;不過,它還是能展現並見證那些被歷史所靜默的、不再出現於此的,以及從記憶最深沉的暗夜升起、縈繞著我們,並督促我們在珍視今日仍擁有的東西之時,對於記住那些死亡的與失去的物事負有責任。」(註2)
簡言之,卡達瓦提醒我們,廢墟攝影所企圖訴說的,反而正是「廢墟不再能訴說任何故事」這件事;但是透過攝影所展現的廢墟影像,仍具有透過凝視遺留之物反思歷史的潛能。同時,廢墟攝影做為「廢墟的廢墟」,除了跟攝影的影像性質,如索引性、時間性與死亡性等關於攝影「此刻獨一性」的特質有關,更是在呼應廢墟的不可回復性、歷史性、朝向死亡之途的寓言效果。因此,攝影與廢墟在某種本質層次上的相似性,也讓兩者得以開展多重層次的對話,以及彼此鏡映的相互凝視。
另一方面,儘管對廢墟之觀看與書寫有著悠久的歷史,廢墟在當代的使用與觀看,依然呈顯為一種相對衝突且複雜的對象狀態。在這裡,我將專注於攝影對廢墟之觀看,以及透過幾個攝影家/藝術家的拍攝行動之案例,探究廢墟與攝影連結之問題狀態。
關於廢墟與攝影在當代的交往,首先便是那歷久不衰、熱切且蜂擁的廢墟攝影風潮。藝術家、攝影家與一般民眾大量紛呈的廢墟探索、發現、再發現、甚至搶救等,諸多結合了攝影拍攝的前進廢墟行動,因而也形成數量可觀的廢墟攝影影像。很快地,廢墟攝影做為一種現象,演變為常在英文脈絡中,尤其是圖片型社群網站的熱門Hashtag#:「Ruin porn」――我試著將之暫譯為「廢墟攝慾」,藉以傳達當代攝影拍攝行動對於廢墟那種近乎色情般的迷戀。另一方面,許多廢墟場景也在「Ruin porn」的交流與擴散過程中成為熱門的地點;也因此,即使是火熱的拍攝場景,在不同的取景與不同的拍攝角度(氣候、時間、機具等條件),拍攝同樣的廢墟位址的兩張照片,也能傳達出截然不同的意義與情感。對此,我們不禁開始思考,不同的拍攝者在同樣的地點所產生的各種可能的差異感受,是否也顛覆了廢墟做為空間/場所/地點所具備的,那原本專屬於特定的人與地方、地方與歷史、人與記憶之間連結的主導性敘事。
其實,我認為這種差異感受與表現正是廢墟攝影做為創作行動所能產生的力量。事實上,廢墟那持續朝向破敗的形象,以及其同時失落自身的歷史、卻又往往被當作歷史物件看待的辨證性質,正是廢墟的存在本身並未言明,但深刻蘊含其中,可以列出一長串的二元性概念。例如,自然與文化、吸引與厭惡、力量與脆弱、潛能與無目的、在場與缺席、棄置或挪用、無常與持續、美學化與拒斥等。於是,我們可以試著議論,所謂的廢墟攝影不但挑戰了廢墟做為空間/場所/地點,其原本專屬於特定歷史與記憶的原始脈絡,廢墟攝影的意義,更應能進一步延伸理解為對各種經典二元論述的跨越和摧毀之實踐。
德勒斯登―天使的凝視
澳洲攝影評論家多納.衛斯特.布雷特(Donna West Brett)在《攝影與地方:1945年後看見與看不見的德國》(Photography and place: seeing and not seeing Germany after 1945)一書中討論1945年戰後德國攝影中的廢墟主題時指出:「攝影對於組織記憶的複雜質地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然而所謂的廢墟美學其實是對各種個人經驗的取消,同時也綜合著喪失感(loss)和迷茫感(disorientation)。」(註3)也就是說,布雷特觀察到,戰後德國廢墟的存在與發生同時也就意謂著將個人的生命記憶與歷史經驗摧毀、抹消,當攝影家們在戰後前往德國各地拍攝並實際遭遇那些破碎與迷失方向的城市景觀時,廢墟攝影做為某種中介,複雜地連結著視覺的與心理的創傷經驗。
二戰結束後,德國攝影家理查.彼得(Richard Peter Sr.)前往德勒斯登展開為期四年的攝影拍攝計畫,並在1949年將其成果出版為攝影集《德勒斯登:一個相機的控訴》(Dresden: eine Kamera klagt an)。攝影集中的著名照片,是彼得在1945年9月至12月之間拍攝於德勒斯登的〈從市政中心塔望向南方〉( Blick vom Rathausturm nach Süden mit der Allegorie der Güte);這張照片如今已成為反法西斯與反新納粹(neo-Nazi)的各種活動中最常見的宣傳圖像。其實在更早之前,這張拍攝在戰後整個德勒斯登城市在戰爭後期的盟軍空襲中被夷為廢墟的照片,早在1951年之後就經常出現在歐洲的歷史教科書、小說、與報紙等出版品上。
此種紀錄災難及其餘波(aftermath)的拍攝手法,比起追求歷史客觀或新聞報導式的描述能提供更好的效果。我的意思是,與許多直接拍攝戰後被夷平的城市廢墟場景(無論是航拍或從殘存的建築物高處拍攝)比較,彼得拍攝的戰後德勒斯登廢墟城市有著更為強大的圖像語彙和敘事效果,這樣的效果來自於照片畫面最前方天使般的雕像,可謂是影像寓言效果最重要的元素。天使的雕像宛如一種準上帝視角的神性身體在此顯影,靜默地凝視著這片被盟軍轟炸過後的狼藉大地。照片不但喚起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像這樣的廢墟城市在戰後的德國四處存在,也是對希特勒和亞伯.史培爾(Albert Speer)的納粹帝國想要在柏林建立「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亞」(Welthauptstadt Germania)大夢之幻滅的最殘酷現實圖像。

布蘭登堡軍事遺跡―蘇聯的遺產
從攝影能記錄現實的觀點,這類拍攝廢墟化與被夷平為空無城市的攝影,不只凝結了城市場景(清理與重建)的持續變動,也無限地推遲了廢墟持續崩壞的狀態。攝影對於捕捉廢墟的謎樣特質似乎有著天生的偏好,這種偏好或許是來自於廢墟與攝影兩者都跟過去與歷史有著密切關聯,並且攝影有著紀錄廢墟的能力,其運作方式就如同在保存遺留物時對過往丟失經驗之彌補。同時,在回應缺席與在場、破碎與整體、可見與不可見等二元性結構中,攝影能展現其複合辨證性。
在1998年至2009年之間,英國攝影家安格斯.波頓(Angus Boulton)展開兩個系列拍攝計畫,主要的拍攝地點都在柏林附近的前蘇聯軍事基地。這些拍攝於屬於前東德的布蘭登堡的攝影作品,波頓將之集結為「蘇聯的遺產」(A Soviet Legacy)系列,以及「41個健身房」(41Gymnasia)系列。在「蘇聯的遺產」系列中,波頓的攝影鏡頭分別從室內與戶外,捕捉已經呈廢棄與毀壞狀態的前蘇聯軍事基地建築物,例如機場、軍營、機堡、瞭望塔、泳池、集合場、餐廳、托兒所、圖書館、教室、辦公室、儲藏室、坑道、吸菸亭、避難所等基地遺跡。而這些影像的一大特色元素,就是那已經斑駁的蘇聯式社會寫實主義宣傳壁畫。這在中國與北韓等共產國家也都是常見的圖騰――那些關於效忠領袖、紅光亮高大全的挺拔軍人形象、對武器的描繪、標語口號之使用。




波頓重返布蘭登堡這個前東德所在地,透過攝影捕捉當年在這些軍事空間裡遺留下來的社會現實主義宣傳壁畫的痕跡。圖像的內容不乏青少年對列寧肖像敬禮、太空科技的發展、核爆蕈狀雲、各式各樣軍人形象等。可以說,前蘇聯的意識型態就這樣展現在建築物的每一面牆上。然而,這些建築物內外的壁畫其實也都已呈現剝落與破碎的狀態,變成地板上的碎屑、隨著室內的破敗一同持續凋零、直至消失。於是,這些曾經做為軍事力量展現的空間場域,如今已成為了軍事政治力量缺席的空間;那些曾經偉大與華麗的政治軍事修辭,現在進入攝影的鏡頭時,已經由普遍毀壞的印象所取代。
「41個健身房」系列影像,同樣來自前東德的所在地,波頓對每一個廢棄的前東德時期的健身採取相同的拍攝手法,如同收集標本般地呈現類似的剝落與破損的場景。這些攝影影像可謂見證了蘇聯軍事力量的失落,或者另一方面也代表西方民主陣營在經歷冷戰時期後獲得某種程度的勝利。這些廢墟攝影不但透過影像捕捉了冷戰的痕跡,也可以做為質問當代政治與軍事秩序的隱喻。如果,廢墟攝影具有某種批判反思的潛能,那麼這些照片可以引發的問題是,當這些強大的軍事力量最終變成廢墟,那麼當代的各種看似強大的政權與軍事力量難道就不會嗎?當然也可以說,波頓的攝影作品傳遞了某種潛在訊息,即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就算是是那些看似永恆的東西,例如碉堡或建築物、或是國際地緣政治的各種力量體系,都終將隨著時間興盛或衰弱,而波頓的攝影作品,便如同做為這種軍事力量的偶然性的隱喻。
事實上,即使像這樣前往冷戰遺跡的拍攝行動,波頓這兩個系列的攝影影像也並沒有傳達明確與特定的政治訊息。對此,如果我們借助大衛.坎帕尼(David Campany)「事件後攝影」(Late Photography)的觀點來看,波頓直接展現來自過去的物質痕跡、透過攝影影像使過往的歷史變得可見(visible),這讓觀者得以透過這些影像連結起過去與現在的想像關係。而這是當代「事件後攝影」對於歷史與事件所開展的詮釋性潛能。

安康接待室―看見與看不見的戒嚴
如果說,攝影、地方、記憶與歷史之間的連結是思考廢墟攝影的起點,那麼,攝影天生的「索引」(indexical)特性,拍下廢墟就等於記錄了歷史?或者問題也可以是,攝影有能力,或是無法捕捉這些來自過去的痕跡?
2020年,攝影家沈昭良前往新店安坑山區,拍攝如今已成廢墟的「安康接待室」遺址。雖名為接待室,其實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擁有當時「最先進」設備的偵訊、拘禁空間;這個當年由調查局和警總軍法處共用的建築空間,在戒嚴時期是關押、留置、刑訊思想犯與政治犯的偵訊型監獄。我想像著沈昭良揣著相機,目光機敏地逡巡於安康接待室建築物內外,在關押、偵訊、辦公、生活等具有不同空間意涵的情境中選擇其鏡頭框取的景象的身影。他拍下了牢房內部、廁所小便斗、通道、地下室階梯、偵訊房、監獄外牆、辦公室、牆面的地藏王菩薩畫像、有窺視窗與布簾並編上號碼的木門。沈昭良寫道:「空間中可見的場景、動線、物件、器具、肌理、漫佈其間的氣息,甚至所處的地理環境,除了使用目的、設計思維與施作工藝之外,也勢必跟當時的政治、權力、治理、經濟、消費、文化、流行和內心想望等複合因素以及所產生的需要、支配甚或控制有關。因此,援引攝影的空間書寫類型,聚焦歷史空間內外的建築實體、物件、痕跡與氛圍,將有可能藉由附著其間的多重寓意,層疊拼湊兼具美學實踐的影像線索,進一步直視景物、貼近歷史也建構時代。」(註4)
攝影家觀看、拍攝、書寫,透過對物的凝視,以及身體穿梭於廢棄建築空間的參與過程,結合想像與歷史知識,在移動歷程的身體書寫空間(同時也是空間對身體之書寫)、影像書寫物件與文字書寫事件的交織體現中,重新想像這個如今被稱為「不義遺址」,已成廢墟場景的安康接待所當年氛圍。攝影家對的廢墟的拍攝行動其實是一種讓自己得以重新置入這個場景的手段;透過沈昭良的文字與攝影,以及他透過物的索引性展開對歷史的逼視,我似乎也參與了安康接待室的廢墟凝視,建構了我的空間經驗。然而,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攝影家的廢墟拍攝行動,就如同廢墟,除了是看見(seeing)的過程,往往更是關於看不見(not seeing)的隱喻。質言之,攝影與廢墟之間的內在關係其實有著豐富的層次,而究其根本,其實就是關乎「看見」與「看不見」的關係辨證。
在每一個身處廢墟的時刻,重要的不是想看見什麼,而是還有什麼是依然可看見的;而透過這些依然可見的(物與場景),看見「看不見」是可能的嗎?對於看見者而言具有什麼意義?這又牽涉到拍攝者做為行動與觀看主體的思考效果,畢竟,面對廢墟,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才是「看見」的意義呢?我的重點是,思考這個依然可「看見」的對象(即廢墟)來自何處(也就是其來由),以及(廢墟)將引領我們前往何處、對當代的我們有什麼重要性,我認為是廢墟攝影最核心的美學意涵,或者是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紐約―餘波與「羊皮紙」隱喻
攝影家喬.梅耶洛維茲(Joel Meyerowitz)在2006年出版的《餘波:世界貿易中心檔案》(Aftermath: World trade center archive)攝影集中,記錄了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在911恐怖攻擊事件倒塌之後的清理過程。他以10x8的大型老式相機(1942 plate camera),搭配35mm徠卡相機,拍攝了超過8000張照片。我們透過《餘波:世界貿易中心檔案》這本攝影集,以及攝影家個人網站依年份日期分類呈現的影像檔案可以看到,梅耶洛維茲在這個長期的大型拍攝計畫中,不只拍攝了當時如山丘般的廢棄鋼筋水泥與破碎建築體、雕塑般的大型施工機具等巨觀的災後場面,以及將災後廢墟場景形塑成充滿崇高感的美學化影像修辭,他更以相機記錄許多在這個災後場景中拾得,經現場人員初步整理分類後的個人物品與屬於某人的日常物件,包含罹難的救難人員與消防人員的工具、警察的槍械等。相較於災後廢墟場景,這些具有私密性的個人物件更是強烈且直接地連繫著死亡、缺席、廢墟與記憶的微觀凝視,指向的是由物件的索引性質的組成的私人的檔案、親友的情感記憶。在這裡,私人物件是無主的、懸置的、等待擁抱的。

關於《餘波:世界貿易中心檔案》中呈現出具有美學崇高感的廣角場景,英國歷史學家連恩.甘迺迪(Liam Kennedy)特別重視其政治性框架與外交意涵;他認為梅耶洛維茲影像中的美學崇高感可以被用來生產當時的美國正經歷「難以言說的喪失」這類的敘事,藉以在外交政策上形塑發動戰爭的有力理由。(註5)攝影評論家莎莉.米勒(Sally Miller)認為不應忽略梅耶洛維茲攝影影像本身的批判性潛能,尤其特別提醒我們留意,梅耶洛維茲拍攝的場景不但是災後的廢墟,更是關於對「廢墟的清理與移除」(the removal of the ruin)過程。(註6)
對911事件後的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做為廢墟地點而言,清理災難現場的過程亦包含著哀悼與療癒的作用,例如後續的處置方式中包含著「保留」、「販售」與「再利用」等手段。「保留」便是在事件地點新建的「911國家紀念博物館」(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 Museum)中保留世貿雙子星大樓殘存的連續壁、立柱、鋼樑、管道殘骸,以及生長於事件地點的「倖存之樹」(Survivor Tree)等具有紀念意義之物;「販售」則是將事件廢墟中清理出來的廢棄鋼材標售至亞洲;而「再利用」便是例如將世貿雙子星大樓鋼材重新熔鑄後,使用在新建造的美國海軍紐約號[USS New York / LPD-21]兩棲船塢登陸艦的艦艏上。

上述這些清理災後廢墟的手段,讓廢墟不再只是「零度地點」(Ground Zero),而是成了是充滿著歷史書寫隱喻的「羊皮紙」(palimpsest)概念,主要是關於反覆書寫的印跡、壓痕比喻,以及「潛能」的暗示。這些後續的處置作為及其代表的重生意涵,都讓「廢墟」與「進展」(progress)兩者間的複雜關係有著更進一步具體化地呈顯。因此我認為,由於廢墟的這種再書寫的潛能,使得廢墟不再只能是單向地朝向死亡與衰敗的意象。此時,廢墟的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將我們拋入時間的矢量中。廢墟的存在,暗示著我們眼前的「現在」,在未來也會變成廢墟,無論是天災或是人禍。於是凝視廢墟的存在,並不是讓我們肯定當前的政治、環境狀況,而是我們有機會可以預先想像另一種未來。而透過對「廢墟時間」的非線性思考,我們便得以進一步連結到前述莎莉.米勒關注到的廢墟的政治性潛能:「廢墟的潛能在於將其『時間性的矛盾』(temporal ambivalence)特性用來搖晃並鬆動霸權論述,如此,一種批判與質問的政治將向我們開放。」(註7)


台灣西南海岸――「台灣水没」的見證問題
攝影家楊順發的「台灣水没」系列是廢墟攝影的另一種美學類型之展現。在這裡,我指涉的除了是楊順發影像作品的質感與風格,所謂的廢墟攝影做為一種美學類型,更是關於他深入拍攝地點,經過長時間的凝視與大量拍攝之後,在後續的影像處理工作中創造出一個個並不存在的廢墟風景;或者說,一個由「成問題的攝影見證」的廢墟影像啟動的環境反思敘事。
對於關注環境與土地的創作思考,陳泓易的評論指出楊順發的海岸踏查計畫與藝術家李俊賢之間的連繫,同時也點出了台灣西南沿海與高雄的相似與差異:「(…)楊順發還是加入李俊賢的《海島計畫》,在 2014 開始進行海岸踏查,從台南開始, 七股海岸一直到嘉義、雲林,整個西南沿海事實上都有與高雄相似的問題,然而神奇的台灣海岸,儘管同樣飽受破壞汙染、國土流失、地層下陷,光是台南、嘉義海邊的風景, 就與高雄大不相同。 」陳泓易認為楊順發的拍攝行動和影像處理手法,「擺脫了模仿『本土人文主義』時的過度明暗的強烈劇場性,而發展出一種近乎法蘭德斯般、多重細工的潔癖所產生清新風格。 」並且,陳泓易也認為,楊順發的攝影將是李俊賢、陳水財、蘇志徹、倪再沁等人自當年啟動《海島計畫》後,那些關於勞動與黑手、海港與工業、到近年的台灣壁畫隊與魚刺客等,這可視為一脈發展的南方風格之路走出新的類型,在時代的前進中發展建構出另一種語言。 (註8)
我認為楊順發的攝影行動採取的主題與手法,訴說的不但是對台灣沿海環境的關注,更是關於對廢墟攝影自身的影像抗辯。一方面,他關切彰化至屏東沿海的環境傷害議題,以拍攝行動留下極大量因地層下陷導致海水淹漫而廢棄的房舍、工寮與廟宇的影像,另一方面,他又在每一幅作品中創造攝影影像之新生命,不斷將大量長時間攝得的影像凝縮成「獨一的風景」、「不存在的風景」或「不可能的風景」。但這並不能很快地說那是假造的風景;毋寧說,這並不適用真與假的二元問題框架。透過「台灣水没」系列,攝影家從按快門者,進入一種由時間堆積的、動員繁複手工的、經過選取與汰除的、多層次的畫面細緻處置過程。同時,作品的呈現形式採橢圓形外框輪廓,而不是攝影作品慣常的方形,這總令我忍不住聯想到中國古典繪畫鏡面裝裱的典雅形式。此外,像是取景採3分之2或2分之1的地平線構圖、以拍攝地點與經緯度為作品標題如〈嘉義新塭鹽場槍樓〉、〈雲林口湖鄉北港溪口魚塭〉等,都是楊順發對於廢墟攝影形式的意見之展現。我所謂的意見之展現,在梅耶洛維茲那裡就是選擇將廢墟美學崇高化、而理查.彼得的德勒斯登廢墟城市在天使凝視下充滿神性之憐憫、以標本式的記錄手法體現在安格斯.波頓的布蘭登堡冷戰遺跡攝影中、而沈昭良則將攝影做為空間書寫類型,關注物件與空間的多重寓意。

楊順發的「台灣水没」系列作品所呈現的,大多是無人的場景、(註9)是人類活動的建築遺跡、是遭受海水鹽蝕衰敗中的廢墟、是荒原般的沙洲水鄉、是環境災害形成的惡水濕地。若接續著前述對畫面處置手法的討論,楊順發的攝影行動確實是扛著相機去目擊、捕捉,然而其作品中的攝影影像不全是「決定性的瞬間」或「世界的某個時空切片」,而是在接合、重疊大量前述的攝影影像狀態的過程中,將畫面組織成充滿持續性時間暗示的「看」與「回憶」的過程。是以,這裡有著從「看」到形成「印象」的這件事所具有的歷時效果與時間厚度,即體現「觀看的經驗」。也就是說,楊順發的創作問題感某方面來自環境批判,也許還有某種土地關懷和南方意識,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楊順發在風景攝影的美學凝視、影像風格營造的種種企圖,那看似溫馴地接受風景攝影的視覺傳統,卻在不斷試圖撐出影像力度的創作嘗試中,已將廢墟攝影的見證性功能看作是一種必須抗辯的影像言說,藉以尋思廢墟攝影的美學格局與批判路徑在當代還有哪些可能性的問題。
最後,投入廢墟攝影的台灣攝影家、藝術家眾多,其中有幾位以計畫型創作長期投入者,我將在另一部分以不同的問題脈絡展開探索。

註釋
- Eduardo Cadava, 2001, Lapsus Imaginis: The Image in Ruins, October, Vol. 96, 35.
- Ibid., 36.
- Donna West Brett, 2016, Photography and place: seeing and not seeing Germany after 1945. New York: Routledge, 19.
- 沈昭良,2020,〈不義遺址:安康接待室〉,台北:台灣光華雜誌。(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a3775060-cbb7-4f87-8d0d-f1ac56cda6d1&CatId=12 瀏覽日期:2020.11.10.)
- Liam Kennedy, 2003, Remembering September 11: Photography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79: 2, 321.
- Sally Miller, 2020,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and theory: concepts and debates, New York: Bloomsbury, 69–70.
- Ibid., 71.
- 陳泓易,2018,〈楊順發的藝術之路 — 從望角到紅毛城〉,台北:非畫廊。(https://www.loranger.com.tw/beyond-gallery/wp-content/uploads/2018/07/楊順發的藝術之路-文_陳泓易.pdf 瀏覽時間:2020.7.15.)
- 「台灣水没」系列多為無人風景,僅少數作品出現人或動物;而以狗的活動與姿態為主角,結合台灣各地沙灘地景的「台灣土狗」系列則屬楊順發近年另一創作系列。